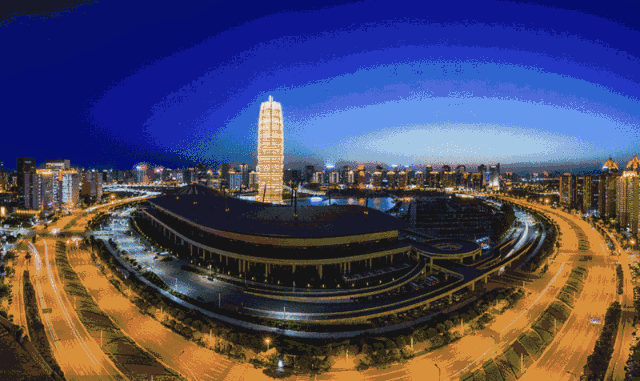我老家門口這棵大皂角樹,是全村唯一一棵最高大的古樹。它究竟有多少歲,誰也說不清楚。生于民國初年的奶奶說,她嫁過來時這棵樹就這么大。生于清末的老爺說,他記事時,這樹就這個樣子。前幾年,縣林業局在大皂角樹的樹干上掛了古樹名木的小牌子,上書:皂角樹,豆科,皂莢屬,樹齡450年。大皂角樹在我家的大門口已挺立了450余年,早已成為小村的地標和象征,成為村人永恒的記憶和鄉愁,成為我永遠的驕傲和牽掛。
年年歲歲樹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若按一代人25年算,大皂角樹已見證了18代人的誕生、成長和逝去,見證了18代人的輝煌和滄桑。18代人如過眼云煙匆匆而過,塵歸塵,土歸土。而大皂角樹雖枝干中空,但依然年年春花秋實,枝繁葉茂,生機勃勃。
聽老年人說,清末修隴海鐵路時,到處征集木材。來人看中了我家的皂角樹,用錛子在樹身的東面錛了一下,留了個記號。后來認為皂角樹的材質粗且樹大難除就放棄了。這個錛過的傷口早已愈合,但現在依然能看到一個巴掌大的痕跡。
據《澠池縣文物志》記載:石盆村皂角樹位于洪陽鎮石盆村。GPS坐標:東徑111°57'58,北緯34°47'3,海撥440m,估算樹齡450年,樹高20m,主干高4.2m,分三枝,胸圍3.2m,樹冠23米。據百度百科:皂莢,別名皂莢樹,皂角,豬牙皂,牙皂,豆科,皂莢屬,落葉喬木,枝為刺圓柱形,小葉柳狀披針形或長圓形;花雜性,為黃白色;莢果帶狀,厚且直,兩面膨起;果瓣革質,褐棕或紅褐巴,常被白色粉霜,有多數種子;莢果短小,稍彎呈新月形,內無種子;花期3,4,5月,果期5到12月。皂莢之名最早記載于《神農本草經》中,李時珍云:莢之樹皂,故名。
初春,和其他樹木相比,大皂角樹的開花發芽姍姍來遲。三月的春風吹過,皂角樹黃白色的花苞小米粒般綻放的時候,空氣中彌漫著淡淡的清香。小小的花苞一天天成果,長大,成熟,漸漸如碗豆莢,如豆角,如小船,如新月;盛夏,濃密的碧綠的樹葉帶來厚厚的樹蔭,新月般碧綠的皂莢掛滿枝頭;金秋,蕭瑟的秋風掠過,枯黃的樹葉蝴蝶般隨風起舞。成熟的皂角果,披上了灰白的一層薄衣,狀如蠶豆的果核滾圓而光潔;深冬,樹葉落光了,灰黑色的樹枝上掛滿飽滿的皂角嘩啦作響,如一樹風鈴隨風搖曳。
皂角砸碎后可起沫,去垢,是天然的清潔劑。在那些物質匱乏的年代,我家的大皂角樹成了全村人的寶貝。媽就時常端著一盆臟衣服,帶著幾個皂角,到不足百步的河里去洗衣服。在清澈見底的小水潭邊,選一塊斜伸到水里的石頭。媽坐下來,將臟衣服在水里泡濕,把砸碎的皂角裹在衣服里,衣服和著皂角,放在石頭上,媽掄起捧槌,"嘭,嘭"的棒槌聲在河谷里回響。
皂角,不僅能供我家和村人洗衣服,還能變成錢貼補家用。十冬臘月,西北風如哨般吹得賊響。睡在堂屋的熱被窩里,能聽見皂角從樹上被風吹下來,落到石堰上"咔,咔"的聲響。夜半,時常被奶奶從熱被窩里叫起來,和奶奶,爹一起去揀皂角。飛舞落下的皂角若落在平地上,趁著月光一眼就能看到。若落到柴禾堆上,玉米桿垛上,小腳的奶奶也會爬高上低去找尋吹落的皂角。
皂角行情好,有外地人來收購的時候,爹便上樹去摘皂角。爹是爬樹的高手,身患心臟病的爹,面對幾丈高的皂角樹,手腳并用,蹭蹭地爬上了高高的樹枝。爹騎在樹杈上,用鉤桿勾住掛滿皂角的樹枝,奮力地搖晃。早已風干的皂角噼哩叭啦掉在地上。我和姐弟們在樹下興奮地揀拾,放在荊條籮筐里。記得有一年,我家的皂角賣了80多塊錢,一筆不小的收入,讓家人寬裕不少。
皂角樹的材質較松且脆,論材質不是上好的木材。但在那個年代,我家的屋基地里沒有材質更好的樹木。記得好象是1982年夏季吧,一聲巨響,一陣大風把大皂角樹上偏東的一枝一摟多粗的樹枝刮斷,掉在了東院鄰居的下東屋房頂上,把人家的房頂砸了個大窟窿。爹把鄰居家的房頂修好,把這段一摟粗的樹枝炕干,讓木匠合了一合大門。大門用的余料,后來我和弟成家后分家時派上了用場。爹給我和弟分家,除了給我倆每家三間廈房,1000多元欠帳外,還有用這段皂角樹枝合成的案板。做案板的木材要細密,瓷實,用切面刀切,跺不起木屑。案板板最好用柏木,柿木,柳木,而這些木頭我家都沒有。盡管別人家沒人用皂角木做案板,但我們并不算寬裕的光景,只有如此將就了。
大皂角樹的樹蔭大,蔭涼厚,垂蔭半畝,如傘如蓋。從我記事起,大皂角樹下,就是村人開會集聚的地方。東院的運來舅是老生產隊長。開會前,運來舅在前街后街東街西街扯著嗓子吆喝:都聽著,都到村西頭大皂角樹底下開會嘍!喊過一遍,村人們三三兩兩,三五成群聚集到大皂角樹下。我家和東院鄰居門口的地上,石頭堰上高低錯落坐滿了人。平時,大皂角樹下,也是村人聚集的場所。張家長,李家短,誰家的兒子不爭氣,誰家的媳婦兒不孝順,誰家賣了一頭大黃牛,誰家的母豬下了一窩小豬娃,天南地北,海闊天空。皂角樹下,儼然成了村人的新聞中心和會客廳。
在村人的心中,大皂角樹因高大古老,早已被奉為風脈樹和神樹。這棵神樹護佑著我世世代代的家人和全村父老鄉親。老年人說,這棵樹上住著仙家,不可不敬,更不可砍伐毀損。那些年大姐和三姐多病,奶奶在院子里擺上豬頭供餉,面對大皂角樹,燃香,磕頭,跪拜,祈禱。
大皂角樹上有無仙家我不得而知,但家人和村人對它是發自內心的敬畏和依戀。大皂角樹有太多的故事和回憶,承載了我太多的記憶和希冀,更是我家的榮耀和驕傲。
誰家若有娶媳婦嫁女兒的事兒,總會到大皂角樹上尋找成雙成對的對把兒皂角。在新人的新被子里放上對把兒皂角,是對一對兒新人最美好的祝福。
我家大皂角樹東南三十多步處,也有一棵東院鄰居李家200歲以上的皂角樹,雖沒有我家這棵高大古老,但也斑駁滄桑。大皂角樹西南二十多步處,原來也有一棵本家侯東林家百歲以上高大的皂角樹。這三棵皂角樹呈鈍角三角形狀排列,按樹齡剛好爺孫三代,像三柱香插在那里,向蒼天祈禱。最可惜的是西南方向那顆皂角樹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被東林家除了賣掉了。為彌補這個缺失,前幾年,我又在大皂角樹的西南方向補栽了一棵三四把粗的皂角樹。這棵補栽的皂角樹一栽上就枝繁葉茂,呈現出無限生機。
上世紀九十年代,弟把老屋拆了建起了新房。把大皂角樹周圍的殘垣斷壁,石頭古堆全部清理整修,大皂角樹一覽無余地完美呈現。
弟的堂屋中堂畫兩側,我編了一聯:耕讀治家皂蔭濃,勤廉傳世溪水長。我請洛陽書畫家張蛟生先生書寫,裝裱,上墻。這付對聯已成為我家的家訓,讓后代永記于心。大皂角樹真如一位老者,一位智者,一位善者,護佑著我家世世代代的男男女女,子子孫孫。
在我幼小的記憶里,大皂角樹生長在我家大門外老磨房的殘墻外,樹干和殘墻中間的縫隙,僅能側身過一個人。我猜想,這棵樹原來并不是老祖先有意栽植的。大皂角樹的幼年一定是一顆遺落的種子不經意地發芽,生長。因皂角樹的材質不是上好的木材,就不會被砍伐做成家俱或蓋房的棟梁。小樹長成大樹,漸漸被人們視為風脈樹和神樹,令人敬而生畏,奉若神明,再也不敢造次了。450多年前的一粒皂角種子生根,發芽,經春花秋實,夏雨冬雪,霜打雷劈,終于長成了六七丈高,垂蔭半畝,大可兩抱的參天古樹。
《莊子》在內篇《人世間》云: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煮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大皂角樹若是中等和上好的木材,可能早已被砍伐,變成了家俱或棟梁。但它因材質平平而無大用,卻活成了一道風景,活成了永恒。就是這棵無大用的皂角樹給人們帶來綠蔭,奉獻碩果,護佑蒼生。
我多想活成一棵大皂角樹,默默無聞地把根深扎在地下,把枝葉高聳入云里,默默地為我深愛的故土奉獻綠蔭和果實,靜靜地為我心愛的父老鄉親,子子孫孫護佑,祈禱。
(配圖由作者提供)
侯建星,男,1967年1月出生,中共黨員,供職于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政府。喜歡文化,旅游,傾情詩與遠方。
老家旅游
視頻河南
今日河南
猜你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