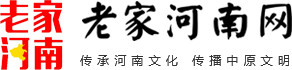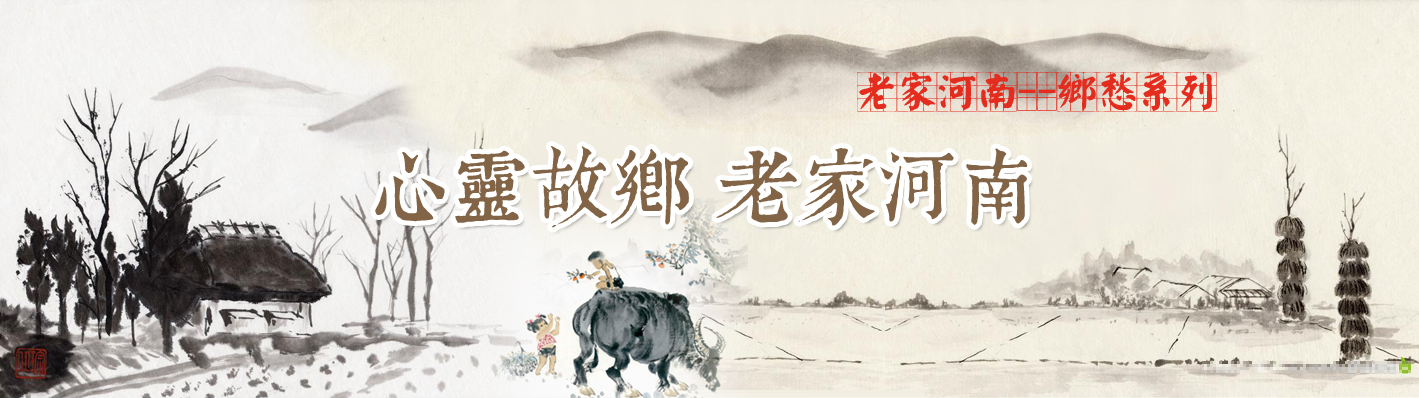黃山遺址出土的玉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3月31日,考古人員在黃山遺址碼頭遺跡發(fā)掘現(xiàn)場認真細致清理。高嵩攝
□來源:河南日報
提起獨山玉,自然想到南陽。想不到的是,距市中心約12公里、獨山東北約3公里處的一座小山丘,自古就有一處繁忙的玉石器加工基地,紅紅火火存在了3000多年。
如今,黃山遺址——這處5000多年前的玉石器加工基地得以重見天日。歷經4個春秋,我省考古工作者揭土拂塵,先后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建筑群、屈家?guī)X文化的墓葬群、石家河文化的堆積層,隱藏在地層之中的文化密碼逐一浮現(xiàn),不斷帶來驚喜。
3月31日,南陽黃山遺址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這是繼入選“2021年度河南五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2021年中國考古新發(fā)現(xiàn)”六大項目之后,該遺址拿下的又一個考古界“年度大獎”。
實至名歸。難怪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伯謙稱之為“中華瑰寶,千年一遇”。
重啟黃山遺址考古發(fā)掘
3月24日,白河岸邊,黃山頂上。雖叫黃山,不過是座小山丘,極不起眼。山頂上,圍擋圈起了考古重地,大棚內,探方連著探方,玉石、陶片隨處可見。
“這又是一個屈家?guī)X大墓,從規(guī)制上看很可能超越之前發(fā)掘的酋長級大墓,它被旁邊漢墓疊壓,我們需要做好規(guī)劃精心清理。”一大早,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黃山遺址考古發(fā)掘領隊馬俊才就蹲在探方內,跟同事們商討如何發(fā)掘新發(fā)現(xiàn)的編號M166墓葬。
馬俊才抽空將遺址“過往”慢慢道來:1959年1月,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黃繼光小隊”配合當地鐵路建設,對黃山遺址進行了第一次發(fā)掘,時間并不長,成果卻豐富。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中對它有長篇的生動描述,考古成果能被當時權威的史書收錄,足見其分量。在河南博物院的第一展廳中,也能見到當年黃山遺址考古發(fā)掘出土玉鉞的風采。
黃山遺址在考古界、在玉器愛好者、在當地村民中都留下了深刻印象。黃山村里,一些上了年紀的村民還記得20世紀50年代的發(fā)掘情況,這塊土地上隨便就能翻到陶片、玉石片。但是,種種原因,這里后來再沒進行過大規(guī)模的發(fā)掘。
2016年,受當地委托,馬俊才組隊對黃山遺址進行大規(guī)模的考古鉆探和調查。他不急不躁,扎扎實實地把調查工作搞了一年多,終于摸清了黃山遺址的底兒:以山頂為中心,面積達到30萬平方米。
2018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聯(lián)手拉開了黃山遺址第二次考古發(fā)掘的帷幕,這一項目最終被納入了“考古中國”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研究課題。黃山遺址,又一次進入了國家級考古研究層面。
馬俊才清楚地記得,那天,他把第一個探方布在了山頂上,以山頂為核心,向外線性擴散。一眼三千年的考古奇觀,就這樣在考古工作者的手鏟中鋪陳開來了。
發(fā)現(xiàn)“龐貝式”史前大型玉器作坊
黃山遺址再次“動土”,考古技師程永剛從一開始便全程參與,對這里的每一處細節(jié)都熟稔于心。
“這是我們2018年發(fā)現(xiàn)的最為重要的仰韶時期編號F1、F2房址以及作坊遺址,都是長方形多單元房基,呈前坊后居的布局。”程永剛小心越過一處處墓葬,指著位于遺址一側的房址說,“除居住生活功能外,這里主要磨制生產玉器石器,地面有很多砂石漿殘存,經過成分分析,大部分為獨山玉石和砂巖磨石粉的混合物,為玉石作坊的定性提供了關鍵證據。”
與此處相隔不遠,是新近發(fā)掘的編號F16、F30、F37的另一組仰韶時期房屋遺址,推拉門道、木骨泥墻、紅燒土是這一時期典型建筑特點。室內的爐臺、工作臺以及散落的石鉆頭、礪石、磨石墩、石鉞生動再現(xiàn)玉石器制作流程。這些房屋分屬仰韶文化早中晚期,它們之間是什么關系,是同一族群連續(xù)居住還是不同族群先后定居?謎團有待進一步揭開。
黃山遺址這些仰韶時期“前坊后居”建筑群,因建筑技術和日常生活細節(jié)完好保留而被專家稱為“龐貝式”遺存。曾兩次到訪的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院院長戴向明告訴記者:“每次去都感覺非常震撼,國內罕見。”
既以玉聞名,黃山遺址出土的玉石料自然極其豐富,以砂巖質的制玉石工具2.3萬余件,另有玉器116件、獨山玉半成品或廢品500余件、玉片3518件、玉料4500余件。其中三塊礫石上繪有褐紅色人物勞動、臥豬、蘭草寫意圖,讓人叫絕。
更讓馬俊才興奮的是,2021年,他們還在黃山腳下發(fā)現(xiàn)了“碼頭”性質的遺跡——直徑約50米的半月形港灣。從發(fā)掘情況看,一條長約500米、寬27米、深7米的人工河道,連接起通往獨山的自然河,并與其他河流一起構成了水路交通系統(tǒng),完備了遺址與獨山、蒲山玉石資源供給體系。
經過幾年的考古發(fā)掘,考古工作者確認了黃山遺址新石器時代玉石器制作遺存,以獨山玉石為資源支撐、其他地方玉材為輔助,大致存在仰韶晚期“居家式”作坊群向屈家?guī)X時期“團體式”生產模式轉變的規(guī)律。值得注意的是,因獨山玉石具有很強的標識性,目前在全國20多個遺址出土的獨山玉器都疑似“黃山造”,或許該遺址生產的玉石器交流范圍已遠遠超出了南陽盆地。
“黃山遺址的考古新發(fā)現(xiàn)填補了中原和長江中游地區(qū)新石器時代玉器作坊遺存的空白。它處在南北文化交流碰撞的關鍵地區(qū)、距今5000多年的關鍵時間節(jié)點,為研究中華文明形成提供了關鍵材料。”馬俊才說。
豬下頜骨的“財富密碼”
與仰韶房址緊鄰的屈家?guī)X文化大型高等級墓葬區(qū),是黃山遺址的另一罕見奇觀。
大墓M77中,雙玉鉞、象牙梳、玉璜、弓箭、骨鏃,400多塊豬下頜骨由小到大排列,分層擺放,環(huán)環(huán)相扣……數千年前如此“豪華”的陪葬,墓主人到底擁有怎樣的權力和財富?
“這些梯形獨木棺、雙玉鉞、象牙飾、單弓、成捆骨簇、少量陶器、大量豬下頜骨,應該是‘酋長’級別墓的標配,他們直接掌管著這個區(qū)域的玉器生產和加工。”馬俊才解釋。陪葬品中,作為財富象征的豬下頜骨最具特色,總數多達1600多個,堪稱新石器遺址之最。
大部分女性墓葬中的豬下頜骨數量為個位數,但也存在特例。在M171女性墓中,頭骨位置有一排細小的骨片,每一塊骨片長約1厘米,兩端打磨圓滑,程永剛說:“推測是串綴起來的冠飾。這個墓的豬下頜骨目前發(fā)現(xiàn)了20多塊,可以看出墓主人的地位不低。”
M172同樣是女性墓葬。不同尋常的是,頭骨左側出土了一把疑似象牙質的編織針。這一把編織針的出土讓考古工作者十分驚喜,專家認為,這些成束骨針應該具有編織功能,進一步清理墓葬,或許可以找到編織材料,不論是植物、動物毛發(fā)或絲,都將為我國史前紡織考古提供重要材料。
黃山遺址出土的上百座屈家?guī)X時期墓葬,是目前豫西南乃至漢水中游地區(qū)這一時期最高等級的墓葬群,頭枕白河、足蹬獨山,排列有序、等級森嚴。墓葬中的人骨遺存幾乎都保存完好,十分罕見。馬俊才說,這得益于黃山周圍的土壤環(huán)境,也給多學科研究提供了一手資料。
經過與北京大學合作進行人骨DNA的采樣測試表明:一直被視作“南方人”的屈家?guī)X人,其中編號M44墓中的個體和黃河流域古代人群有著顯著關系。“M44墓中的個體是遷徙、貿易還是戰(zhàn)爭原因由北至此,還有待進一步研究。”馬俊才說。
“考古奇觀”的新期待
從考古大棚走出,站在黃山頂上眺望,麥苗青、油菜黃、桃花粉,玉帶般的白河從東邊山腳下流過,西邊是已經湮沒的古河道,蜿蜒通向遠方。幾千年前,“黃山造”的玉器就是從這里輾轉走向中原、流通江漢。
與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發(fā)達的玉器制作相比,中原地區(qū)新石器時代玉器較為稀少,以玉聞名的黃山遺址因此也得到了考古界的特別關注。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趙輝認為,黃山遺址距離獨山不遠,獨山有獨山玉,這是人類最早利用玉這種優(yōu)質材料的證明。這里從仰韶時期到屈家?guī)X時期一直從事玉器加工,雖然文化變化了,產業(yè)沒變,而且社會復雜化程度越來越高,為反映史前社會發(fā)展過程提供了資料,非常難得。
面對腳下這片與玉相伴的黃土,馬俊才也有甜蜜的“煩惱”:“整個遺址層層疊疊都是寶,房摞房、墓摞墓,常常出現(xiàn)仰韶時期、屈家?guī)X時期制玉作坊和房址、墓葬相互疊壓打破現(xiàn)象,手鏟稍一挖,就碰到其他時期的東西,抉擇困難。”
越是復雜,越要規(guī)范。細致的發(fā)掘流程、多學科的研究方法、邊發(fā)掘邊保護的理念,馬俊才探方里的幾把刷子在業(yè)內頗有名氣。專家這樣評價黃山遺址發(fā)掘工作:墓葬清理得非常精彩,非常細致,連弓矢的痕跡都做出來了,這在新石器時代墓葬考古中十分罕見。
優(yōu)越的地理位置、保存完整、現(xiàn)代因素干擾少,黃山遺址跨越幾千年且文物遺存豐富集中,具備極高的展示價值。河南省文物考古學會會長孫英民認為,黃山遺址兼有南北文化整合的特點,是中原地區(qū)新石器時代的代表性遺址,非常適宜建設國家考古遺址博物館和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它的發(fā)掘研究、保護展示,必將為南陽副中心城市建設提供強大的歷史文化支撐,讓“行走河南·讀懂中國”的文化品牌越來越響亮。
老家旅游
視頻河南
今日河南
猜你喜歡